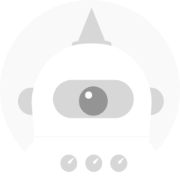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林正茗,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0年初夏,北京街头乍现地摊烟火。我和小区附近的小吃摊摊主们成了朋友,与他们吃喝闲逛,寻找悬浮生活的意义。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605个故事
故事时间:2020年
故事地点:北京
01 寻找“附近”
北漂的第三年,我日益觉得自己正过着一种 “悬浮”的生活。
在京两年,工作团队重组三次,搬了六次家。起初还和室友、同事联络感情,后来发现不管多要好,人迈入新的环境,最先抛却以前的生活。因异地感情淡漠和前任分手后,我对关系愈发不信任,将全部身心放在工作上。
时间被工作、通勤挤压到所剩无几,朋友们分散在朝阳、海淀、丰台,每个人都被KPI捆绑,见一面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一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这座大都市的过客,另一方面和故乡的人情社会脱节,城市留不住,家乡回不去,就先拿健康和时间兑换一点点财富。
好几位朋友两年换了三份工作,在每一家公司都主动996,周末努力健身、上课,而这种努力和不断地变动究竟能带来什么,一切都是未知。这座城市永远不缺更年轻的进击者,如学者项飚所说,我们像蜂鸟一般拼命振翅,才得以将自己悬停在城市的上空。
年初,我和一位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合租,不久便碰上疫情,经济动荡,原本牢靠的工作也变得摇摇欲坠。
她在一家以加班闻名的广告公司工作,有时通宵开会,最晚一次第二天上午十点才下班回家,工作之余拼命接私活。两人忙得脚不沾地,怕稍微放松就被行业抛弃。
找房找得仓促,租了套一居,两个女孩住一间卧室,一人一张床,起初开玩笑像是回到大学宿舍。但没多久,我朝十晚七,她朝十二晚十二,作息错开,即便都早早下班回家,顶着在工作中被耗尽了社交热情的疲惫的脸,也相看无言。
5月,我重看许知远对项飚的访谈,项飚提到一个概念“附近”,指跟你日常生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方和人。人们通过外卖、网约车、淘宝,人不用和他人打交道,就可以快捷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需求,“附近”消失了。
北京没有附近。人人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已经捉襟见肘,更难说与其他人建立连接,哪怕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
6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一个年轻男孩从背后快步超过我,撞了下我的肩膀。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他如此着急回家,是要去做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点完外卖,在游戏和网剧里结束这一天?
我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值得奔赴的。
抱着这样消极的心情,我发现回小区的必经之路上,停着几辆由电动三轮车改装的餐车,刚刚下班的人们停顿在了那里。我住的小区位于北京东五环一座地铁站附近,5月之前,因为疫情,行人稀少,相视走过也会匆匆避让,很少看到这样热闹的情景。
02 深夜烧烤摊
几辆餐车围成一个四角,西南角卖的是麻辣烫,摊主是一对夫妇,男人穿黑色背心、人字拖,面庞并不老,但秃顶和啤酒肚较早降临。他对面是一家烧烤摊,摊主是一个黄头发的男孩,右臂上布满青色纹身;烧烤摊旁边,是一家炸鸡摊,招牌上“买一斤送半斤”的优惠诱惑着往来的行人……
年轻的白领和附近超市、餐馆、按摩店工作的人们,走进四角区域中,脚步都慢了起来。五块钱买一纸袋炸蘑菇,十块钱一碗炒河粉、一个身材纤瘦的女孩只要了一根一块五毛钱的烤肠,这是拥有起送价门槛的外卖无法满足的简单快乐。
我选择在烧烤摊停留。摊主叫阿辉,原本在一家连锁烧烤店上班,疫情冲击后,阿辉所在的店员工工资几乎减半。阿辉早就考虑过单干,这回下了决心。
阿辉人缘不错,来给他帮忙的人不少。一个男人问我,吃点啥。他叫阿龙,是个自来熟,摊位边和他一样站着的好几位黑衣男人,都是阿辉的朋友。他们都是东北人,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主动出来帮朋友招呼客人。
烧烤摊支起的小桌旁已经坐满了人,我无从分辨谁是帮手、谁是客人。一个北京大哥坐在最角落的凳子上,手机里播放着短视频,脚边放一瓶啤酒,兀自唱着歌。区别于其他餐点,阿辉的摊位更像一个朋友的聚会,来帮忙的朋友想吃什么,阿辉便烤什么。烤串不断地被端上塑料小桌子,像是一场迷你的、粗糙的流动盛宴。
一有客人光顾,阿辉便招呼着食客们加入烧烤摊的群聊。出摊一周左右,群成员已经近100人。进群第二天,我在群里@阿辉:今天什么时候出摊?阿辉回复:7点半左右。阿龙跟楼,发的文字也带着热闹劲儿:晚上都出啦(来)哈(喝)啤酒!
那些夜晚都是如此,没有人着急回家。一个穿白色波点长裙的中年女人总是在深夜下班,路过摊贩点要一份夜宵,这是她每一天的晚餐。摊主们猜她在单位是个领导,因为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大声训斥下属。但这会儿,疲惫爬上她的面部,她慢慢地起盘子里的食物,柔声聊起自己在老家读书的女儿。过了零点,有人喊了一句:谁现在在家能睡得着啊?在家也是玩手机,来这多好啊!
那天在烧烤摊,我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归属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
03 摆摊人中的有产者
6月初,“地摊经济“更热了,摆摊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一个拖着行李箱卖衣服的女孩,高挑漂亮,她说自己是模特经纪人,我刚摸了摸T恤的质地,她立刻把衣服套在身上展示效果:“是不是挺好看?”
一个矮小、微胖的女人卖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是鲜花,有时是玩具。端午节临近,她的布袋上铺上了五彩绳。她30多岁,原本在超市工作,因为超市裁员,她失业后摆摊暂时过渡。
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端坐在矮凳上四处张望,脖上挂着一个收款码。女孩看着往来的行人,一边吃着小零食。她旁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见我凑近,招呼女孩道,看看姐姐想要什么。我问她为什么出来摆摊?女人指身后的小区,我们就住这儿,我女儿算术不好,带她来摆摊,练练计算题。
我在纸箱里挑了一包甜卡力和百草味的五香花生,女人对女儿说:终于有姐姐肯买你的东西了,你高兴吧?这位母亲坚持将零食以半价卖给了我。
摆摊人中的有产者不止一位。淼哥今年35岁,北漂近10年,他开着一家旅游公司,做欧洲旅游地接业务,公司有七八个员工,疫情冲击旅游业,淼哥只好暂时把公司关了。出来卖麻辣烫。不为赚钱,手头有事儿做,心里不那么慌。
陪着淼哥出摊的是他的妻子红莲。红莲是北京人,开两家美甲店,他们在附近的小区有三套房子,自己住一套,父母住一套,还有一套直租出去,月租金4500元,在外地还买了一套海景房,“因为女儿喜欢去海边玩,这样比较方便。”
6月6日是个周六,加班的白领少了,生意很清淡。但淼哥认真地招呼着客人,宽粉就是红薯粉,鱼丸是安井的,西兰花养颜,鸭胸肉也是最好的……
2019年,淼哥公司收益不错,2020年年初,淼哥提了一辆车,首付25万,月供5000。1月底,中国新冠疫情爆发,淼哥做的是欧洲地接,竟然接了几个单子,“那时国内的人都往国外跑。”
4、5月份,本该是欧洲游旺季,欧洲疫情爆发。淼哥起初想观望一阵。5月底,看出疫情短期内无法结束,他将员工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其他行业寻找就业机会。他们有的先去做了电商、线上教育,淼哥最乐观地预计,消费者对旅游行业恢复热情至少要等到年底。虽然家里有存款,红莲的美甲店也重新开业,但自己停滞的事业还是令他焦灼不已。
比起之前每天坐在家里干着急,他的生活变得充实。出摊累,他晚上也不失眠了。“没摆摊的时候什么都想:公司房租交着,员工工资发着……想得天花乱坠。一卖麻辣烫,只想着如何把这锅麻辣烫烫好,怎么能多卖出一份。”
淼哥做过小包工头、销售、房产中介,2015年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起初生意惨淡,为争取大客户,他主动帮客户搬家,打扫卫生。2016年年底,旅游公司业务开始盈利。那时“动动手指,打几个电话,几千块钱入账”, 一度过上了花钱时没有感觉的生活。常和哥们一起出去喝酒唱歌,一次花个八百一千;女儿参加一次夏令营一万多块……
疫情冲击到有产者坚挺的生活。家里消费习惯已经形成,如若不采取行动,可能坐吃山空。现在,他晚上七点半出摊,站到凌晨十二点,一晚最多能赚四五百块。休息日和雨天生意更差,可能只能赚一两百块。他再没和哥们一起出去吃过饭,想聚会,就去彼此家中小酌。
那个晚上,我跟着淼哥出摊,到了夜晚11点半时,我觉得腿酸胀得站不住了。淼哥还站着,零星几个行人,看了看已经不那么新鲜的蔬菜,走掉了。那个穿波点长裙的女人过来,说自己嗓子哑了,想吃点清淡的,挑拣了几片菜叶后,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十块钱给做吗?”
淼哥没有犹豫:“给做。就是一块钱也给做。”
04 八里桥不眠夜
深夜小吃摊的最主要客户是夜间工作者,比如外卖小哥、滴滴司机。他们需要补充热量,又不能太贵,炒面炒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耿记炒面服务的就是这些人。
大部分小吃摊的招牌都是红色,耿记是绿色,中间嵌着一个英文字母,“healthy”。摊主陈风念出这个单词,发音不甚准确,但释义没错。“就是绿色、健康的意思”。
陈风是江苏人,摊子叫耿记是因为妻子姓耿。他今年40多岁,初中学历,知道的几个英文单词,都是跟正在念初一的小儿子学的。
小儿子是他来北京的原因。小儿子先天漏斗胸,孩子5岁时,陈风带他来到北京做手术,因为几年后还需要二次手术,担心来回折腾,陈风决定让儿子在北京上学。
夫妇俩一直开炒面摊维生,卖到半夜收摊,回家收拾一下,凌晨两点,妻子耿丽先睡下,第二天早上6点,她要起来给儿子做早餐。陈风则骑三轮电动车去八里桥农贸市场,购买第二天的原材料。
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八里桥农贸市场,是首都副中心的菜篮子,每日出入人流量达2万多人。难以想象凌晨两点钟的市场,我提出想要跟陈风去进一次货,他答应了。我们前往市场的路上,陈风手机提示音提示微信进账,耿丽还没睡。陈风说:今天的生意太差了,妻子不甘心,换了个位置又出了会摊。
八里桥农贸市场里,流动餐车上卖的粥和豆浆还冒着热气,这是为市场里深夜工作的人们准备的。6月的夜晚清凉,大货车拉来市郊刚采摘好的白菜、香菜、西红柿……沾着清晨露水的蔬菜整齐码放在摊位上,卖菜的和买菜的人彼此精神奕奕地还价,手指在计算器键盘上敲得飞快;一辆辆载着各类青菜的电动三轮车在拥挤的菜场里灵活地穿行,这里藏着北京的折叠世界。
货装好后,我们驶离市场,路过通惠河,岸边停着两排长长的汽车队伍,都是来八里桥农贸市场进货的车辆。
返程的十几分钟里,令我惊讶地,陈风和我聊起了几个名字:陈丹青、王小波和海子。他复述了陈丹青讲过的几句话,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他一点也不困。直到我们聊起他的小摊,他的声音才从远方拉回现实。
为给小儿子做手术,夫妇俩来到北京,将大儿子送到县城的私立学校,大儿子却开始翻墙去网吧,沉迷网络游戏,最终没有考上大学,现在二十七岁,还是沉迷游戏,不喜与人交际。好在小儿子手术很成功,现在健康好动,在学校的长跑活动中表现优异。不过,陈风和耿丽合计过,小儿子无法在北京初升高,他们计划,等儿子初二就回老家。
到家了,我们三个人把所有的货物卸下。接近凌晨四点,远远地听见几声鸡鸣,月亮挂在纷乱的老式电线间。在灯光昏暗的厨房,耿丽在水盆里洗了一把樱桃,樱桃有些已经烂掉,陈风把坏的挑出来,我们三人分享了那捧樱桃。
耿丽可以睡一会儿了。尽管一个半小时后要起床,给儿子准备早餐,而陈风睡到中午,要起来洗菜、切菜,为晚上出摊做准备。
05 小小的喜鹊
有段时间,我每晚都会下楼和摊贩们聊天,在弥漫着烟尘和孜然味儿的摊位间,我认识了更多的摊贩。
卖烤冷面的柳青今年64岁,几年前公公中风瘫痪,丈夫在家照顾,她北漂赚钱,支援两个儿子结完婚买完房,她准备这几年再为自己攒些钱养老。柳青嗓门大,说方言,会和男摊主开荤味的玩笑,性格比一些男摊贩更强悍。其他摊贩的车子被扣了都拿钱去赎,但柳青从来不去,抄一辆她就自己再买一辆。
卖炸鸡的刘辰在摊位里生意是最好的,他个子不高,人很沉默。他在这附近卖炸鸡已经一年了,积累不少回头客,但疫情冲击下,他的每天的收入比之前缩水了一半,摆摊难以支撑在北京的1000多元的月租、老家每月3000块的房贷以及儿子每月的补课费。他晚上12点收摊,早上6点钟起来进货,进完货跑一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一天能多赚100多元。只是白天跑外卖加上出摊,他每天只能睡不到6个小时,聊天时直打哈欠。
不久之后,我听说楼下遭遇了一次突击检查,其他摊贩都跑掉了,只有刘辰,电瓶没电了,没能跑掉,他需要花2000块把餐车赎回来,那是他摆摊一周的收入。
和摊主们接触快一个月了,混了个脸熟。我毕竟白天要上班,渐渐地也不常去了。只在下班看他们不忙时,同他们打一声招呼。有时加班很晚,远远地看到几盏亮着的灯,心里也觉得挺暖。哪天管理严格起来,摊位稀稀落落,我心里也空荡荡的。
前几天,我又去和刘辰聊天,他把车赎了回来,把摊位换到一个更隐秘的地方。和我说话时,眼睛总是警觉地盯着路上远处驶来的车辆。他告诉我,他听到消息,下个月这里就不能摆摊了。
我们说话的间隙,烧烤摊的伙伴来了,看了看他的车前灯:“坏了啊。”
灯只剩下一个壳子,罩在碎掉的灯泡上。刘辰上前把它拿下来,车被扣那天,车灯在匆忙间被撞碎了。我问刘辰:“在北京这么久了,你有想过要离开北京吗?”
“没想过。”
“没想过?”
“舍不得。”他不好意思地笑了。2月,他在河南老家,许多在北京的食客给他发微信:什么时候回来?想吃炸鸡了。他迟迟没回来,100多人的顾客群最后只剩下40多个。
回北京跑外卖后,附近加油站的几个员工连续几天给他发微信,想要吃炸鸡。刘辰有天中午没去跑单,去市场买了十几斤鸡腿,在家里炸好给他们送过去,只收了他们7、80元钱。“没有跑外卖赚钱,但他们想吃嘛。”
说话间,又来了两位顾客,将他摊位上剩下的炸鸡皮也买走了。他收了摊,同我说了再见。
阿辉的烧烤摊还在营业,我想要再和他们聊聊。刚说明来意,帮阿辉送单的女孩招呼我:“你想聊什么,我来跟你聊。”
这是个高个的短发女孩,每天骑着摩托车帮阿辉送单,背影挺飒。在烧烤摊遇到她几次,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
她仰头喝着啤酒酒:“你说想和我们聊聊,大家为什么摆摊?还不是为了生活吗?我们都惨到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你还要写我们……”她接着说:“你觉得你坐办公室、吹着空调的人,你和我们是一个世界的吗?”
那天我离开后,没再去打扰过任何人。如果说这些夜晚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附近”,那么我学到的是,悬浮生活自有其意义。在那个小小的盛宴上,在那个分享樱桃的夜里,我们彼此安慰,共同震动翅膀。
我想起那个从八里桥农贸市场返程的夜晚,我和陈风经过一株梧桐树,他突然放慢车速,指着路边的一只灰喜鹊:“这只喜鹊很特别,它是一只灰喜鹊。别看它小,它很聪明的。”我们没再说话,一起看了喜鹊一小会儿。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