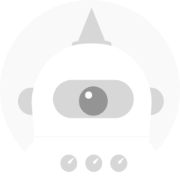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来源蓝洞商业,作者赵卫卫,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进来的老铁们,点点小红心。”少年马虎的爸爸正在快手的直播间里唱《离家的孩子》,他喝红了脸,时不时的跟老铁们互动,兴致到了,儿子马虎在一旁开心地跳起了舞,背景音乐放的是他最爱的快手神曲《摩托摇》,这一幕也是《棒!少年》里一家人暖心时刻。
而在《杀马特,我爱你》里,曾经的杀马特们对着镜头回忆起曾经的“至暗时刻”,他们的快手号被官方整顿,收入骤降,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回去打工。劲爆的“凤舞九天”舞曲响起来,曾经的杀马特女孩在快手直播间的镜头前尽情摇摆。她说,“自己也想跟其他主播一样,白天打工晚上直播赚钱。”
这是两部纪录片里关于快手的“惊鸿一瞥”。
《棒!少年》、《杀马特,我爱你》这两部近期备受热议和关注的高分纪录片,都给了快手植入“免费广告”的机会,即便快手并没有投资过它们。
巧合的是,两部作品都开拍于2017年,那是抖音崛起的前夜,也是快手在中国下沉市场遥遥领先的高光时刻。两部纪录片同样都对准了原生家庭残缺、历经坎坷的农村少年,以及他们背后真实的中国。
电影《棒!少年》讲述的是一对原生家庭残缺的孩子被棒球改变命运的故事,他们被强棒天使棒球基地从偏远山村带到北京从事棒球运动。主人公少年马虎和小双性格迥然相异,一个小混混,一个忧伤抑郁,他们在棒球队里发生种种矛盾,但最终都收获了成长。
而《杀马特,我爱你》更像一个社会学样本的集体回忆录,两个小时的片长,没有导演视角,50多位曾经的杀马特少年在镜头前讲述自己过往的遭遇。原生家庭的痛苦挥之不去,他们十几岁就开始外出进厂打工,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又封闭的劳作里,杀马特标志性的头发成为他们生活里最大乐趣。
目前,《棒!少年》正在院线上映,豆瓣评分8.7,21000多人看过;《杀马特,我爱你》举行了小型的展映,豆瓣评分8.7,9200多人看过,评分已经说明了其不俗的口碑与质量。
一个是棒球改变农村少年命运的励志故事,一个重新打量被误解和伤害的杀马特群体,《棒!少年》和《杀马特,我爱你》两部纪录片的问题意识导向,都是对社会现实关照的产物。
它们注定与快手出品的首部纪录片《国产艺术家凌凌》等作品有着云泥之别,前者雪中送炭,后者锦上添花。
“我是一只流浪狗”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这是余华1993年就在《活着》的序言里写的,《棒!少年》导演许慧晶对此深以为然。
这或许可以解释,《棒!少年》里的主线是少年马虎和小双因为棒球而成长,而他们出身于亲情缺失的家庭,棒球学校也多次面临拆迁的命运等等现实问题,都是纪录片里的背景。
少年马虎来自宁夏的贫困县,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很早就离家出走,所以马虎一直是一个街头小霸王一样的存在。棒球教练把他带到北京,他跟棒球队的少年打架、上课调皮捣蛋,身上有足够多的戏剧性。
比如训练结束,教练给小棒球队员们讲话,调皮的马虎只能在远处罚站。教练说,要把队员们培养成一群狼,一旁委屈的马虎说,“我就是一条流浪狗”。而可贵的是,马虎在棒球学校慢慢锐变,最终融入集体,与队友们一起站在美国棒球比赛的现场。
《棒!少年》前前后后改了40多个版本,但少年马虎伴着快手名曲“摩托摇”跳舞的场面从来没动过,即便很多人提出过质疑,也只是修改了呈现形式。
导演许慧晶觉得,马虎跳舞的片段是他最爱的内容之一,因为那是马虎从原生家庭里带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孩子从儿童长成少年时的烙印,“它是属于马虎的精神世界,对他很珍贵。”
能够在正片中保留快手名曲的部分,一方面是导演许慧晶的坚持,一方面也是爱奇艺的宽容。纪录片《棒!少年》的主出品方是爱奇艺,爱奇艺拥有《棒!少年》的定剪权,但实际上给了导演很大的创作自由度。
遗憾的是,即便《棒!少年》是迄今为止今年豆瓣电影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但在上映一周的后今天,其累计票房刚刚达到400万。
院线纪录片之外,爱奇艺未来还会上线《棒!少年》的剧集版,从6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中,找到在纪录片中无法得到完全展现的东西,都会放在6集的纪录片剧集里。
许慧晶也想,未来一直把这群棒球少年记录到他们18岁成年,在他们当中,学习成绩好的会进入专业院校,也可能去当棒球教练或是外出打工,总之记录到他们人生下一个岔路口,会是另外一个精彩的真实故事。
审美自由是起点
如果说,《棒!杀马特》动人的是看到了贫困少年因为棒球而改变命运,那么《杀马特,我爱你》的可贵在于,杀马特群体们已经长大,他们在镜头前平静地讲述自己曾经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命运。
跟《棒!少年》的开放式的结尾迥然相异,《杀马特,我爱你》的结尾把问题和盘托出。伴着歌声,曾经的杀马特说起了自己贫乏的童年,他们都来自困顿的农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父母外出打工成了留守儿童,家庭的变故像一根钉子扎在他们心里。
就像《棒!少年》里充满戏剧张力的马虎一样,《杀马特,我爱你》的关键人物是曾经的杀马特教主罗福兴。
罗福兴说的非常直白,杀马特都是一群没有父辈给他们打下基础的人,所以他们出来的选择只有进厂。“没有别的选择了,进厂肯定无聊,你得找一个有趣的东西,而头发就是一个有趣的东西,玩车玩别的你也玩不起,只有玩头发。”
《杀马特,我爱你》揭示了“杀马特之所以成为杀马特”的残酷现实原因。
与《棒!少年》充满故事性的叙述不同,《杀马特,我爱你》没有戏剧性,没有导演视角,只有杀马特们在镜头前叙述,导演李一凡只想告诉观众,他们的生命真的很贫乏,远比不上他们的头发好看。
《杀马特,我爱你》导演和制片人都是川美教师李一凡,制作资金来自深圳建筑双年展、广东时代美术馆和腾讯新闻。某种程度上,这首先是一个独立影像艺术作品,因为杀马特这个特殊群体的题材,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
《杀马特,我爱你》中有大量的杀马特所在工厂工作环境的实拍短视频,这些都是李一凡花钱从他们那征集来的。
本来对于征集的过程,李一凡想写个征集启事,类似于摄影大赛之类文绉绉的东西,但同事一直没写出来,最后罗福兴简洁明了的把这事干了,他在征集标语很简单,只有两句话:不要押金。日赚千元不是梦。
这才是跟杀马特年轻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随后,真实工作场景的短视频纷至沓来,环境之差出乎李一凡的意料,曾有小孩告诉他,为了多赚钱去了24小时工厂,每天在工厂打盹,一个月下来体重从110斤变成了80斤。
某种程度上,短视频平台也是李一凡所反思的问题对象。
在东莞石排镇与杀马特接触的那些日子,李一凡通过快手搜索杀马特喜欢的关键词,搜索本地视频后,他看到的网络世界与之前截然不同,“那时我才开始渐渐理解一点他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社会的阶层割裂是非常严重的,都不是一般的严重,再加上现在的这种数字霸权,AI总是选你喜欢的,你这个阶级该看的东西让你看。最后让你的眼界越来越窄。”李一凡在采访里说。
快手的难题
自从2016年的《底层残酷物语:一个视频软件里的中国》发布以来,“非主流”和“土味”成为快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痛点,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鸿沟,造成了极端对立的社会情绪。
这促使快手在极力改变其品牌形象,急迫地争夺一二线市场并展开让快手破圈的行动,以试图让上层人士理解快手文化。
快手的第一部自制纪录片《国产艺术家凌凌捌》是找曾经的网红苏紫紫做的,他们把镜头对准的是新裤子主唱彭磊、快手创意红人手工耿、24岁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装置艺术家徐震等人;快手的首部卡车司机电影《他是我兄弟》,票价3元,已经有超过18.2万人购买;快手也推出了自己的首个女团KSGirls,宣扬她们代表着快手上所有平凡的女性用户……
这些精品化的内容,都承载着快手破圈占领更高市场的野心,但它们始终是在快手体系内的小范围实验,没有在更大范围空间里取得市场和口碑共鸣。
究其本质,其单一的文化视角也与《杀马特,我爱你》、《棒!少年》这样更具反思和问题视角的纪录片形成鲜明对比,没有什么比真实持久的观察更能打破传统话语体系的桎梏。
《杀马特,我爱你》完成了对杀马特群体的祛魅化过程,更是对社会现实的不宽容的批判。在李一凡看来,杀马特只是用头发的改造来拯救生活贫乏,而网络封杀和社会的妖魔化攻击,导致杀马特剃掉头发重新回到了沉默的流水线工厂,重新回到生活贫乏。
拍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54岁的李一凡觉得自己内心更柔软了,他不是没看到杀马特个体上的诸多缺点,但深入探究杀马特的成长环境和社会现状之后,他说:
“我心里特别柔软,记得我去采访伟哈哈的时候,特别心疼,听他讲完我抱了抱他,我眼泪都出来了,以前从没有过。”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