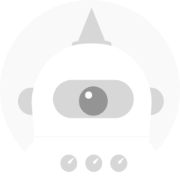1936 年,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索斯比拍卖行竞得一批封存了两百多年的牛顿手稿。手稿内容被公之于众之前,所有人都相信,牛顿是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近代科学家,一位理性主义者。然而,这批手稿向人们展示了「近代物理学之父」的另一面:牛顿还是一名炼金术的狂热爱好者。他一直相信点石成金的可能,为此投入了近三十年时间,从事长生不老药和贵金属提炼的研究与实验。他留下的手稿中,有关炼金术的内容超过了 100 万字。
凯恩斯读罢手稿,感慨万千,「牛顿并非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那些魔法师中的最后一位」。评论家们则说,「从手稿公布之日起,牛顿肯定不再只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了」。
关于炼金术的研究手稿并不能掩盖牛顿在近代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但毕竟让我们知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即使是最顶级的科学家,也有「不科学」的时候。
这么多年过去,牛顿孜孜以求的「点石成金」,从理论上,通过核试验就能实现。与此同时,「新潮」的科学家也早就不把心思放在「点石成金」这样的「改造世界」的事情上,他们想「改造人类本身」。
11 月 26 日,深圳学者贺建奎利用基因编辑婴儿的事情一经曝光,立即引发持续风波。很多人都好奇,既然「基因编辑婴儿」已经出现,那么设计一个「完美婴儿」离我们还有多远?甚至有人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有可能出现经过基因编辑的「超级人类」?
虽然科技工作者们说,在技术层面,这项试验相对简单,相当数量的实验室都具备条件和能力。距离设计「完美婴儿」甚至「超级人类」非常遥远。过去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前技术下,试验的安全性得不到保证。研究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还会把麻烦遗传给每一个子孙后代。但是,学术共同体依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担忧。
26 日,国内 122 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认为试验存在严重的生命伦理问题。27 日,140 名艾滋病研究专业人士发表公开信称,「坚决反对这种无视科学和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反对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未得到证实的基础上,开展针对人类健康受精卵和胚胎基因修饰和编辑研究」。权威科学传播机构英国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也发布了 20 位科学家对此的评论,有学者称:「用孩子的健康和希望换取廉价噱头,简直卑鄙!」

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事儿,大家很担心
科学研究永无止境,但人类社会始终有共同遵守的生命伦理底线。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突破生命伦理底线的科学研究,不少最终都变成了悲剧,留下永难抹去的伤痛。
2011 年 3 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一份数千页的秘密实验记录,里面详细记录了 60 多年前,美国一名医生用危地马拉囚犯和精神病人研究梅毒的实验过程。
1946 年至 1948 年,美国政府派遣医生到拉美国家危地马拉进行医学研究课题。研究员约翰·库特勒调研的内容是青霉素对抗性病传播的效果。当他和其他医生认为患者不够多时,会让实验对象「接种」性病病毒。他们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故意通过患病妓女让其感染性病,诸如梅毒、淋病,受害者多达数百人。
报告称,受「性病实验」感染的包括危地马拉的军人、监狱里的囚犯,甚至还有精神病人。「危地马拉监狱、军营以及精神病院被选为实验地点,一共有 696 个实验对象,而感染性病的受害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未得到足够的治疗。」
这起实验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 2010 年 10 月,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医学史教授苏珊·里维尔比无意中发现了库特勒的实验记录,才迫使有关方面为这项不道德的实验道歉。

在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也曾发生过如此悲剧
现在,国际社会对将人当做「小白鼠」的医学实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有比较明确的界限。被视为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行为,被学术共同体所拒绝。而这条底线,也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才逐渐构建起来的。
1918 年,也就是牛顿手稿被拍卖的 18 年前,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一个名为弗里茨·哈伯的德国化学家。原因是他在 1909 年首次从空气中制造出了氨,使人类从此摆脱了依靠天然氮肥的被动局面,农业得到了加速发展,当时严峻的粮食危机得以缓解。赞扬他的人都说:他是天使,为人类带来丰收和喜悦,是用空气制造面包的圣人。
也就是这样一位「圣人」,在获得诺贝奖前成为了杀人于无形的恶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望「为国分忧」的弗里茨·哈伯为德国军队高层想了个「致胜妙招」:通过化学合成制造有毒物质,投放到战场。随后他担任德国化学兵工厂厂长,负责研制和生产氯气、芥子气等毒气。
1915 年 4 月的一天,由他负责制造的 168 吨氯被释放到空气中,借风势扶摇而上直奔敌方军队。黄绿色的气体滚过满目疮痍的战地,负伤的兵发出惊恐的尖叫。烟雾所经之处,绿草瞬间变成铁灰色,窒息的飞鸟纷纷坠落。数千人瞬间丧生,战场变成了屠杀之地。毒气战首次在人类战场出现。许多人诅咒哈伯说:他是魔鬼,给人类带来灾难、痛苦和死亡。
一战后,1925 年,经过国际社会努力,达成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和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并最终发展为 1997 年生效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科学探索的初心,永远都应该是保护人类
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二战期间,用人体做实验的行为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德国纳粹分子借用科学实验和优生之名,用人体实验杀死了 600 万犹太人、战俘及其他无辜者,这些人被纳粹统称为「没有价值的生命」。主持这些惨无人道实验的,除纳粹官员外,还有许多医学教授和高级专家。
实验种类五花八门。为了进行人体低温实验,研究预防和治疗低体温症的方法,研究人员将囚犯泡在冰水池中数个小时;为了测试人体是否先天拥有对结核的抗体以及研究结核疫苗,在诺因加默集中营,研究人员将结核杆菌注射入囚犯肺部……更为我们熟知的,是日本 731 部队在东北用活人进行冻伤、细菌感染、毒气实验,惨无人道、罄竹难书。
二战后的 1946 年,为了审判战犯,纽伦堡法庭制定了人体实验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上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规范,并公布于世。《纽伦堡法典》之后,1964 年召开的第 18 届世界医学协会联合大会上,又发布了比《纽伦堡法典》更加全面、具体、完善的关于人体实验的国际文件《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宣言制定了涉及人体对象医学研究的道德原则,对以人作为受试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提出了伦理原则和限制条件。正是不断汲取惨痛历史的教训,整个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了共识,划分出了对人体本身的研究中,「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
诚然,「基因编辑婴儿」与「毒气战」、「以活人做细菌实验」有着本质的区别。小二罗列这些极端案例,也并不是要像否定过去那些实验一样将「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彻底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罗列这些案例,只是想说: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应该突破科学共同体和整个社会所遵循的伦理底线,甚至以此为噱头,沾沾自喜。因为从历史经验看,我们并不知道,底线一旦突破,人类即将面对的是怎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