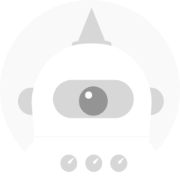1989年出生的毕赣被誉为华语电影的下一位大师,这位从贵州凯里走出来的年轻导演虽非电影科班出身,但其26岁时执导完成的首部电影长片《路边野餐》却一举囊括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名奖等多项业内有目共睹的重量级奖项。
对于一位创作者而言,作品本身才是最诚实的背书。
在毕赣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公映之前,他的从艺生涯可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形容。内行认可毕赣的禀赋,外行则敬畏世俗大奖,不会有更多的人去质疑他业已取得的成就。
直到那些从“抖音”上挤出时间、准备“一吻跨年”的年轻观众走进电影院,这位本该置放在艺术与市场的评价标准中的新锐匠人,伴随着影评网站上喷涌而出的“一星差评”被强行拉下神坛。
一部文艺片制造了比商业片更成功的营销案例,而它的创作者却在赚到钱之后被贴上了“烂片导演”的标签,与《地球最后的夜晚》相关的一切,恐是这位素来对“成功学”嗤之以鼻的候补大师始料未及的。
文艺与商业
当中国观众念叨起一部预售票房过亿的国产艺术电影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将其与去年《江湖儿女》6900多万的总票房做对比。作为现如今国内最受主流认知的艺术导演,贾樟柯却未在“以成绩说话”的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亩三分地里,向那位同样坚持文艺路线、以故乡小城为元素的后辈做好表率。
而在受众审美并无明显提升的背景中替艺术电影打了一个翻身仗的毕赣,相形之下就显得“成功”很多了。如果说姜文的《让子弹飞》定义了“站着挣钱”的模板,《地球最后的夜晚》便无疑走了一条“躺着挣钱”的新路,虽然它的成绩实质要归因于营销而非剧作。

很多人或许会问:毕赣的新片究竟是什么成色?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不同的人在乎不同的答案。在《十三邀》里,毕赣告诉许知远,他对于共识不抱希望——“语言有太多的障碍、欺骗性、假定性,反而电影更真实一些。在我生长的整个环境里面,沟通都是无效的,没有用”。
事情如毕赣所言,沟通是需要条件的,它至少要建立在听懂彼此或者试图听懂彼此的坚实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就只能想别的办法创造条件。
假使《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营销团队没有推出有针对性的策略,这部制作成本达5000万人民币的小众文艺片的最终结果一定是铩羽而归。但与此同时,它是有价值的、是受得住内行讨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可如果就像已经发生的这样,《地球最后的夜晚》用了烂片惯用的商业手段为自己做宣传,它既赢得了文艺青年与迷影青年的吆喝,又赚够了“战狼粉”和“前任粉”的钞票,与此同时,它仍是有价值的。
既然营销方式不会影响内容本身,那它何乐而不为?
毕赣在《吐槽大会》里阐述过一个观点:在他的认知中,电影不分文艺商业,只分好和坏。比起“为什么N多人给《地球最后的夜晚》打一星”,更有意义的问题应是“一部电影好和坏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在毕赣的学生时代,他意外接触到了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一部“评价很高、都说很好”的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经典。毕赣对这部电影最初的印象是看不懂、上当了,但之所以他后来作为一位享誉国际的导演、并被称为“中国的塔可夫斯基”,正是由于他对自己的认知进行了反思,同时不断学习与领略电影美学。如果毕赣像如今那些吐槽《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年轻观众一样,在键盘上打诸如“什么垃圾、自恋狂”之类的差评,他无疑不会成为今天的毕赣。这里体现的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人格差距。
一言蔽之:烂片把自己包装成好片,好观众会骂烂片是烂片;而好片把自己包装成烂片,烂观众会骂好片是烂片。
技艺与作品
《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之前,媒体提及毕赣的时候,动辄以“长镜头”始以“长镜头”终,彼一时的公共舆论似乎很需要毕赣充当一个有代表性的冉冉升起的符号,就如同它们在此一时很需要后者在“沽名钓誉”乃至“欺世盗名”的位置上坐久一点,便于自己充分挖掘新闻素材。
实际上呢,毕赣欺谁了?他既没有欺骗人,更没有欺负人。他所挑战与颠覆的,只是华语电影固化已久的叙事逻辑与产业秩序,对他所有作为的描述与丈量,圈定在艺术审美与文学品鉴的疆界才是明智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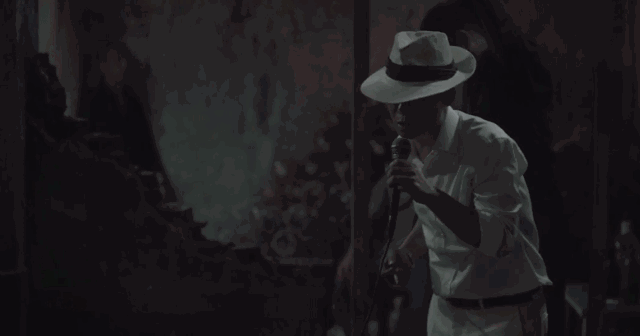
对于毕赣的这部新作,电影学者刘宇清评价道:“小镇青年的《乡愁》(塔可夫斯基的代表作)。毕赣的爱恨,尽管格局无法和塔可夫斯基的信仰媲美,但取法大师的努力本身就值得珍惜。在中国电影里,拍梦境、记忆和意识、无意识,除了毕赣,还有谁呢?”
在影片里,毕赣长镜头中亦真亦幻的凯里给俄狄浦斯情结提供了容身之处,主人公罗纮武“一十二年弃置身”的记忆、梦境与现实,在逐渐掩去细节的绳索之后,相互织结成一个莫比乌斯环,在那些历经漂移的黏稠身份背后不断纠葛,又形成统一。毕赣在形式上致敬了塔可夫斯基、王家卫和安东尼奥尼,在实质上致敬的其实是克里斯托弗·诺兰。
相对于以往观众熟悉的叙事,毕赣是反叙事的,他不是为反而反,而是以跳出逻辑的方式谋求更大的逻辑。这个逻辑的指向,是一个男人不断寻找他失去的女人的故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母题”是简单的,但毕赣讲故事的手段却在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面前略显复杂。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毕赣不是故作高深,也不是雕琢痕迹,这只是他作为一个“手艺人”的惯性。

拍完《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之后,毕赣坦言,他真正想讲的东西都已经在这两部作品里不打折扣地讲完了,比起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他更看重的是艺术对自我的训练——“拍电影你要强迫自己思考很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解决那些关系,如果当它无法解决的时候,怎么表达那个关系。”对于毕赣而言,电影是一条救赎之道,生活中所有让他感到不安和困惑的事情,放到电影里反而让他有一种安全感,他将这个过程称作“把它关在那里”。
在毕赣身上,那条“一位导演的早期作品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的观点得到了应验,他形容自己接下来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去复刻别人的脑中宇宙:“拍电影这种事情,它不像做一个作家,作家一定要有那个东西才能写作。但是作为一个导演,你不一定非要拍心里面的东西,你可以拍别人心里面的东西。你有手艺,你手艺被锻炼出来了,一样可以。”
郁结与关照
毕赣和贾樟柯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双子座。
在我的理解中,双子座真正成熟的标志,是舍弃聪明和技巧转去做更耗费耐心的功课。贾樟柯就是这样成熟的,从《天注定》开始,他一反“故乡三部曲”里娴熟操弄的符号化指涉,以朴素、平实、直白的基调捕捉时代变化与人的情绪。贾樟柯坚信从对现世启蒙与关照的角度来看,最粗糙的平铺直叙也要胜于最精妙的隐喻配置。《道德经》里讲“大巧若拙”,以上便是一位双子座艺术家“大拙”里的“大巧”。
虽然毕赣在艺术风格上还处在自我完善的阶段,但是当他面对许知远讲出“先关照人,再关照人类”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他在思维层面的早熟以及人设上的不虚伪——“首先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没有什么忧虑,没有什么郁结,然后才开始有心情去关心人”。
《地球最后的夜晚》所经历的预售神话与口碑滑坡,几乎都是与毕赣同龄乃至比他更年轻的青年人造就的。观影者在极短时间内对毕赣反戈一击的效果,在院线经理的排片表上可谓立竿见影。他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并不关心的那位年轻导演其实是如何关心他们的。
在《十三邀》里,毕赣向许知远提到,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焦虑,行动力也差,最重要的是,他们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焦虑。在物质生活方面,年轻人越来越拮据;在精神生活方面,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是一片空白,是无意识的,这非常要命。
毕赣:那我是该提醒他“你现在要焦虑一下”,还是不提醒他呢。很多时候我都欲言又止,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我的姿态也不对,我应该和他们一样。
许知远:这个折磨你吗,或者说困扰你吗?
毕赣:我刻意地让自己别那么好为人师。尊重别人的生活,尊重别人的逻辑,尊重他自己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去为他做这个提醒。就好像他生活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我突然拿了一个东西进来,那个东西是一次性的,可能会打破他的生活,可能就没有了——那个水果吃完就没有了。
许知远:那你觉得侯孝贤的电影是试图去说这个事情吗?
毕赣:更相反,我觉得侯导不会去强加教育某一种观点。他只是在旁边等你,拍出你的样子来给你看。
为什么人们应该尊敬乃至热爱文艺工作者,因为一位真正的文艺工作者,他对于“人”的态度是温和宽厚的,是彬彬有礼的,是克制收敛的。他们不会提高声调、宣讲布道,一面收割中年人的钱,一面收割年轻人的智商。在毕赣这里,我看不到他所喜爱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所指出的那种现象——“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受之无愧地接受什么”。
毕赣的意见是,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成功学和励志题材,正是因为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挫败感与无力感,这实际上是社会造成的。“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挫败感,好像你年轻,你天生就应该有挫败感。”
当毕赣为那些年轻人感到担忧的时候,他所担忧的对象却仍在耗尽自己的全部心力去关心那些抽象的、宏大的事关主义的叙事,关心捕风捉影的娱乐八卦,关心体育赛事的位次成败。他们既不像贾樟柯电影里的青年那样,充满了对生活的反抗意识;又不复侯孝贤电影里的青年那般,热衷于捕捉“形而上”的虚无。
他们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庸碌而充实、热血又盲目,受鼓惑而欣悦,受诱导而不自知,就像他们攥着一张《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票,却指望能在里面看到低俗偶像剧里才会有的“浪漫”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