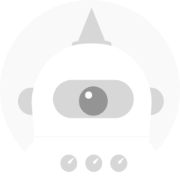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三声,作者 刘丹。
北京是Zak离开英国后到达的第一个城市。
那是2007年1月,出租车从机场开往前门要一个多小时,路程是Zak从家到曼彻斯特机场的三倍。Zak看着窗外由荒芜的城郊变成高楼林立的市区、人挨着人的景点,弄不准自己是否要在这个城市定居。那年夏天,他学会跳过菜单上的中式英文,用中文在餐馆点牛肉面和几种盖饭,发现了鼓楼各种好玩的“地下”场所。
2019年的夏天已经过去,Zak还在北京,鼓楼给了他留下的理由。十多年里,他体验过这个城市的不同侧面:二环之内,窝在胡同里,“舒坦”的北京;四环开外,挤压在丽都高档小区里,生活以工作为圆心,“枯燥”的北京。
Zak在后一个生存场景中赚到了钱,但总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最终回到前者。他租下一间大杂院里的平房,和房东签了五年租约,终于有了一个符合自己生活要求的房子。他从小就喜欢逛跳蚤市场,现在家里收藏的老物件越来越多,有儿时的熟悉感。
离开英国时,他想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离开丽都后,他知道了这种生活的确切模样,“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精神的质量。”
回龙观在五环外,距离鼓楼30多公里,常住人口近30万,被称为“亚洲第一大社区”。蝴蝶公主是30万分之一,从小到大,她心中的北京也存在某种割裂感:“观里”,居民楼密密麻麻,少有大型商场;“观外”,三里屯对于蝴蝶公主而言远得像在另一个城市。
今年暑假,她抛下对“高档场所”的紧张感,第一次逛了三里屯,“居然有这么多好玩的店,北京真是一个大城市。”
作为一个从小“超级无敌虚荣的人”,蝴蝶公主的穿搭与三里屯脱节。她最近着迷于00年代的风格,常穿豹纹吊带、荧光色旗袍,水钻恨天高。受限于钱和阅历,这是她最具性价比的自我表达方式。
和痴迷老物件的Zak不同,蝴蝶公主的复古情怀不限于特定的东西、场所,而是一种野生的、富有本土特色的“过时”审美。她喜欢具有年龄感的声色场所,不随时间变化的欲望实体。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与城市发展步调错开,像Zak一样停在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或者像蝴蝶公主一样与北京更为缓慢的角落保持同步。发展越快,城市在时间或者空间尺度上分裂出的“两面”冲突越强,怀旧或者回望就会成为一些人的本能需要。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
01 | 无用主义
进入30岁后,杨函憬很难熬夜加班,对喝酒蹦迪也没什么兴趣。唯一让他深夜也有动力出门的是去逛鬼市。来北京后,他专门去过几次大柳树鬼市,12点出门,凌晨3点顶着月光回来,“表示自己还活着,我能够在夜市出现,证明我对这个城市文化感兴趣。”
旧物仓从厦门一路开到广州、深圳、珠海和北京等地,杨函憬现在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剩下的时间全国各地跑项目,被各种人问,“旧物仓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七年前,旧物仓是厦门东浦路上一间“破烂儿”仓库,里面装着破产负债的杨函憬和他用近十年时间收集的旧家具。曾经帮他采集旧物的师傅们回乡盖起了别墅,杨函憬在没有空调、晚间断电的厂房仓库里,招待打着手电筒来的债主和买家。
“卖破烂儿”成了他意料之外的收入来源。旧物仓由此起步,但转折点不在于商业模式,而是杨函憬又一次疯狂行为:2014年厦门修建地铁,许多老花砖要被拆除。杨函憬本能觉得,这对城市来说可能是不可逆的损失,于是开始成吨收购这种“水泥块”。再次面临破产,杨函憬发起一场“花砖众筹”,全国2000多人参与,一共筹到了190多万。
在杨函憬看来,这是一种“无用主义”的胜利。“旧物可能在物化的过程中是无用的,但在情绪、情感,美学心理上是有用的。”
Zak家里“没用”的老物件越来越多,他好像从北京的“游客”变成了北京的“居民”。
来北京只是因为偶然刷到一张单程打折机票。飞机落地前,他对北京的认知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他某个“典型老外”朋友口中有武当山、能学功夫的地方;二是一些70年代的武侠电影,以及高中课堂上学过的中国近代史。
Zak先是在前门大栅栏住了两年,2012年左右搬到丽都,和一个朋友一起在家里办英语培训班,后来又拉了那时的女朋友入伙。小区很高档,家里什么都是新的,没有适合摆放老物件的地方,“我觉得我心里就没有营养,因为很少出来玩。”
在丽都的时候,他们的客户主要是家在顺义的富人家庭,钱好赚,事也多。一位合伙人想把生意继续做大,Zak和他理念不合,于是退出公司,一年后和女朋友分手,“我们将来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她要的是别人对她的尊重,我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
几年后再相见,两人都有了不同的心境,从前的合伙人已经在顺义开起了有名的教育公司,Zak成了胡同酒吧里的小老板。
刚开酒吧那时候,Zak在门口收破烂的板车上淘过两个老闹钟,价格都在10块钱左右,如果他愿意,转手再卖个300元不成问题。但价格并不是老物件的绝对衡量尺度,比起“售卖”,或许“交换”才能实现老物件的价值最大化。
这两年Zak搬进了一个大杂院,毛坯房,他自己找工人来建了个独立洗手间。尽管还是租的房子,Zak觉得生活的临时感终于消失了,家里摆放的东西越来越多,收集老物件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了。
他现在已经有了上百个老闹钟,一部分在家,有30多个摆在酒吧门口的置物架顶层。架子高,钟又摆得密,得站在沙发上才能够着,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的指针已经停转了,有几组是重复的款式,还有一个钟面上衬着文革招贴画,“我知道是假的,其实不是文革时期的,但是我喜欢”。
有一款闹钟上贴着金色的东方明珠塔浮雕,随着时间流逝,金属光泽被锈迹覆盖。Zak看到它就会想起自己去上海旅游的见闻,但他也承认这种设计有点土,“我自己不会摆在家里”。
这个老钟被放在架子的角落,有个客人一眼就发现了它。多年以前,他家的显眼位置曾摆着同款。那是单位发给父亲的奖品,又新又洋气,他至今都记得父亲把它摆在桌子上的样子。
02 | 胡同鬼市
9月,Zak连办了两次“胡同鬼市”。
如今Zak从交道口的十字路口往鼓楼走,一路上能看到20多家空置待租的店铺。因为前两年整顿“拆墙打洞”,Zak的酒吧从方家胡同搬到寿比胡同,后来又来到郎家胡同。现在酒吧两公里开外是南锣鼓巷,在Zak眼里,这块被规划出来的娱乐区和当年的方家胡同完全是两种氛围。
老物件越研究越上瘾,摸着这个线索,Zak发现鼓楼这一片儿的同好还是不少,于是就把“胡同鬼市”办起来了。“胡同鬼市”开在酒吧小院儿,十来个喜欢收集老物件的玩家,每个人分得一张旧木桌,从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没有人抱着一定要卖出东西的心态来摆摊。“未来商店”的胡子和二昆在正对小院儿门口的地方摆了一桌老玩具。大部分玩具现在已经停产,乍看上去带着点灰败感。圈外人只能凭借童年记忆认出诸如“忍者神龟”“米老鼠”之类的形象,听到价钱后,本能反应可能是:这么贵?
这话一落地,买卖基本就吹了。胡子和二昆觉得,老玩具的价值不在“贵不贵”,而在“懂不懂”,“如果他对玩具有了解,或者能说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个买卖才有可能做成。”
胡子从小喜欢看漫画和动画片,上班后偶尔翻闲鱼或者是淘宝看到小时候熟悉的玩具,慢慢地就开始收藏和研究。童年记忆被老玩具激活,回过头来再去看那时候的动画片,常常会收获和小时候不同的观看体验。
“比如说看到哥斯拉的玩具,就会再看一下《奥特曼》,然后就发现剧情跟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特别蠢特别逗。看《奥特曼》又会发现其他玩具,就这样循环下去。”
因为喜欢听爵士乐、看老电影,胡子认识了他的女朋友二昆,恋爱后二昆在胡子的影响下开始喜欢老玩具。最近他们把家搬到了通州,搬家的时候装老玩具的箱子收拾出了20多箱。
最近两人都辞职在家,想做些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生活要精打细算,他们还没舍得在新家安置玩具展柜。怀疑自己的选择,担心路走窄了的时候,两人就各拿一个老玩具,你一段我一段地编故事。回过神来,半天时间过去了,桌子上不知不觉摆满了玩具。
“这就是玩具的意义!”二昆说,“你可以通过玩具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精神世界都放到这里面来。”
一定程度上,对音乐、电影,玩具的爱好相互影响,“老玩具可能与电影有关,或者与动画有关,与以前的文化历史或者乐队有关,这些都可以让我在看到玩具的时候想起来,再去听一下乐队,看一下电影,把我带入一个新的东西。”
听说Zak要办复古市集,Ryan第一个报名。他俩是在一个黑胶唱片市集认识的,就像Zak所说,音乐和收藏的圈子交叉度很高。
根据Ryan的保守估计,他手上单是黑胶唱片就有上万张。量太大,家里到处都是,甚至厨房、阳台上都堆满了唱片。Ryan想过“断舍离”,也不排斥卖出去一部分唱片,但念头往往终结于四个字:有市无价。
他是在“打口时代”建立音乐体系的那批人,上世纪90年代,国外唱片业发行过剩,数以百万计的打口磁带和打口碟被当作塑料垃圾倾销到中国。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商机,另外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不同于港台流行乐的新世界。
在五道口和新街口的小店里,两者形成地下交易的默契。买家收到风声提早守在店门口,老板开门,把装着唱片的硬纸壳箱子往外一扔,就像扔一块肉。一帮人扑上去疯抢,手里抓着,屁股底下压着,凭瞬间的眼力抽出几张CD,谁也不确定今天能买到什么。
Ryan毕业的时候正赶上“非典”。在网络时代来临和监管收紧前,打口碟的生命周期被短暂地延长了一会儿。城市停摆,Ryan的实习搁置了,但他一点也不焦虑,每天早上坐着302路公交,像上班一样定时定点从团结湖出发到五道口,一圈子朋友吃吃喝喝、谈论音乐,一块买唱片。
很快一切恢复运转,Ryan实习、就业、辞职、做自由职业者,开酒吧,总能见到当年和他抢唱片的那批人,“反正都没有脱离大的音乐圈子”。
03 | 民间神仙
3月,蝴蝶公主办了一场联谊舞会,主题是庆祝她主办的交友杂志《缘来是你》创刊1周年暨停刊纪念。整场舞会成本10000块,花光了蝴蝶公主攒下的压岁钱。原本她想把场地定在年轻人常去的夜场,后来要么包场费用太高,要么是场地方不接受她的风格,最终她来到一家中老年舞厅。
与杨函憬带有理想色彩的“无用主义”相比,蝴蝶公主对“过时”的迷恋来自更加实用的需求,经济拮据和物质欲望构成了蝴蝶公主“又土又华丽”的两面。这个念大四的北京女孩穿着来自淘宝爆款和外贸店的打折衣服,大多色彩饱和、剪裁贴身,看起来像90年代离开小县城去南方打工,而后衣锦还乡的小姨。
联想无所不包、“按需造神”的奶奶庙,或许比较容易理解她“又土又华丽”的质感。易县县城北的“奶奶庙”依山而建,山顶香火最旺的庙原本挂着“救苦殿”的匾额,后来便于理解,直接换成“正殿”两个黑体大字。这里寺庙密集,神仙亲切,用塑料板搭个棚子,棚里放个纸壳箱,各种材质的神仙带着同样用黑体字书写的“名片”坐在箱子里,“厂家批发,就地开光”。
蝴蝶公主没去过奶奶庙,看过相关报道后就被吸引了,这成为她的审美来源。与奶奶庙相比,她觉得自己作为“蝴蝶公主”的各种尝试都不够真实和野生。
此前,学校布置过一个“无用装置”的课题,她根据民间各种人为致残的传说做了个“花瓶姑娘”,把一个假人头放在花瓶上,给她起名叫丽丽,以丽丽的形象在平台上直播。借由丽丽的眼睛,蝴蝶公主见到了更多奇怪的人,比如丽丽的朋友,一个文绉绉的男主播,每到深夜就变成聒噪的变装女郎;还有丽丽的仇人,一个听丽丽说她来自中国后,立刻破口大骂的男人,他警告丽丽,下回就说你是日本的,别给中国人丢脸。
听说快手上有很多“妖魔鬼怪”,她也想成为其中一员,于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捏着嗓子说话的家庭主妇,想让人们讨厌她、骂红她。但奇怪的是,总有人留言说觉得她像是从哪个年代穿越来的。骂她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夸她声音好听,人很温柔。
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或许能由“奶奶庙”给出一些答案。
在精英文化的解读中,奶奶庙是经济挂帅下的粗鄙审美。毕竟奶奶庙所在的河北易县曾经是离北京最近的贫困县,去年刚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探访奶奶庙的媒体也感到疑惑:奶奶庙香火旺盛,高峰期能吸引超过一百万人朝拜,不少人专门从北京赶来,跪在从旧椅子上拆下的跪拜垫上,面色虔诚——有时候,审美是根据经济和欲望定制而来的。
关于这些“民间神仙”,甚至于大部分老物件、网络“妖魔鬼怪”的多维解读空间,都来自某种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来的分裂感。
Ryan去年在四惠地铁站出口开了个酒吧,单是威士忌就有好几百种,日常还有演出和艺术展。四惠站是换乘站,北京地铁1号线和八通线在此交汇,连接着市中心和通州新城,上班族多,人流量大,他觉得这里有点东京街头的意思。
开店一年多,Ryan不得不承认:四惠地区没有喝酒属性。来店里喝酒人不多,“大家宁可打车去三里屯,也不愿意在家楼下酒吧喝一杯。”偶尔办活动,四九城里的人来到他的酒吧,他恍惚觉得自己好像在鼓楼。
而鼓楼,不仅有Zak迷恋的胡同,live house,各种酒吧,也有苍蝇馆子、修自行车铺子、理发店,各种因为低价房租聚集起来的外地人。整顿“拆墙打洞”,胡同门脸上的店面被封,有的邻居去看热闹。后来大杂院里头也被拆,胡同里的酒吧和小生意都少了。
胡同里的居民和店家也会有摩擦,酒鬼在街头吵架,邻居往酒吧院子里扔玻璃瓶。Zak他们的酒吧和邻居相处得很好,他喜欢观察胡同,还有来来走走的人,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但在一些城市规划者眼中,“那是很脏的东西,要把它抹掉。”
蝴蝶公主小时候会有种自卑情结,不敢进出咖啡馆和图书馆这种“高档”场所,后来她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假装高档,她就是喜欢“土”的,基于本土文化诞生的东西。
配合《缘来是你》“本土、艳俗、廉价以及诙谐,但很强调真诚”的风格,舞会当晚,蝴蝶公主穿着大红色的蛋糕裙,在绿衣白裙的伴舞簇拥下手拿绸扇跳舞,《butterfly》的旋律交织着台下的年轻男女和大爷大妈们的欢呼声。蝴蝶公主在舞厅认识的微信名叫“飘”的阿姨应邀前来,一直玩到了凌晨三点。
新和老都不是绝对概念。年轻人想要寻找的昨天,正是“飘”的年轻岁月,也是迪斯科音乐响起时,舞池中自由轻盈的舞步。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