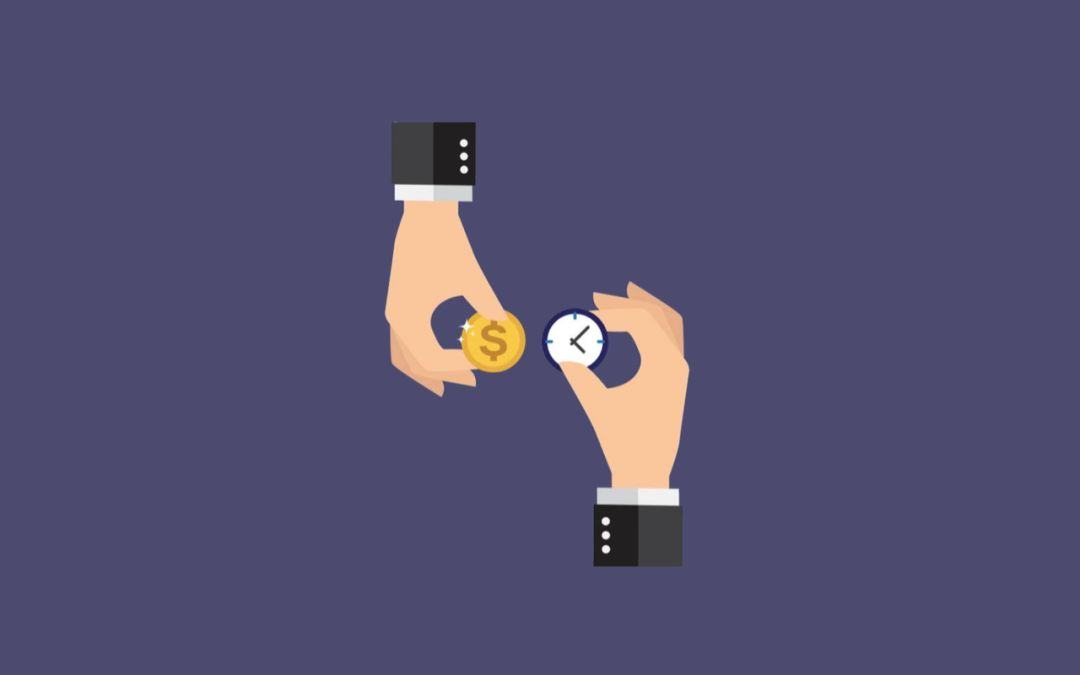
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深几度,作者吴俊宇。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原本并没有那么重要,和第一个十年跨越千年相比,它仅仅只是波澜中的一丝水花。
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无人知晓这个新的十年会发生什么。
但它的第一个月很快昭示了自己的重要性。
一
遥远的澳洲大陆无声燃起了一场天火,考拉在哭泣,袋鼠在逃窜,人们无家可归,湛蓝的天空被烧成了血腥的红色。
它是在上一个十年的尾巴悄然燎原的,人们真正意识到它的威力时已是新的十年。天火肆虐之际,曾任社会服务部部长的总理正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八小时航程外的夏威夷度假。他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
第一岛链上的秃头无赖让整个蓝营在炎热和寒冷中打摆子。曾穿越威权时期的白发老人在青壮派“老贼”的骂声中黯然离去。
一批老练的新旧政治精算师算无可算,最终陷入历史困境。从伦敦政经学院走出的绿营女政客冷若冰霜,却靠丝毫不犯错的话语以及对岸的失误裹挟着年轻一代稳固了自己摇摇欲坠的位置。
第三个星期,一场瘟疫降临了东亚的中心,并悄然弥漫到了半个世界。史无前例,一座一千万人口的城市被封。
和澳大利亚人的后知后觉一样,瘟疫发生的真实时间还要往前再推一个多月。因为地方官僚体系的僵化,它的时间被群体怯懦所掩盖了。诡异的是,这座城里的人在农历新年的第四天忍无可忍,打开窗户唱起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这场瘟疫弥漫的同时,美洲大陆上,一代篮球巨星科比坠机离世,他再也见不到凌晨四点的纽约。
那位推特治国的高龄商人领袖在社交媒体上敲下了“那真是可怕的消息”。在这天,他还转推了另一条有关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消息,“我们缅怀因纳粹政权犯下可怕罪行而丧生的数百万宝贵灵魂”。
仅仅一天之后,英伦三岛选择脱离欧洲,礼貌疏离的英国人选择和浪漫激进的法国人以及严谨沉稳的德国人挥手告别。
法国骑士和德国战车依旧紧紧绑在一起,在新旧霸主的夹缝中彷徨迷茫。而在六天前,欧洲两位核心和东亚中心那位核心拨通了跨越大洲的电话。
二
爱尔兰诗人詹姆斯·乔伊斯100年前在诗歌中吟咏:
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试图从中觉醒。
但小半个世纪前,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却在《洪堡的礼物》中借诗人洪堡之嘴哀叹:
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只想在这场噩梦中好好睡上一觉。
睡觉——回到东亚大陆,人们宅在家里,只能用睡觉这种方式躲避瘟疫。
在躲避瘟疫的日子里,翻开了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作者彼得·沃森的中文版序翻开就一股浓浓的“纽约时报风”,查了查彼得·沃森的百科资料,发现他果然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重要的是,他仅仅只是一位记者。1998年开始才在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看这本书在不同国家的书名也是很有趣。
在英国是《惊骇之美》(A Terrible Beauty),原因在于,他认为爱尔兰诗人那段“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是整个20世纪的墓志铭。
在美国是《现代思想》(The Mddern Mind),理由是美国人太过浅薄,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更为朴实的文字审美”,看待事物更是缺少历史思维,对古典时代较为冷漠。
到了中国才变成了《20世纪思想史》,在彼得·沃森眼中,中国人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过去,但20世纪的中国缺少像约翰·罗尔斯一样能够提出“无知之幕”的学者,不足以撼动世界对政治框架的理解。
无论是文学、艺术、科学领域,也都缺乏深刻影响世界的思考者——他希望能够用这本书提醒中国读者所面临的挑战。
我一直怀疑记者出身的人能否用一部鸿篇巨制来阐述自己对整个20世纪的理解,然而彼得·沃森不管做得怎样,他终究还是做到了。
他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的话说:
互联网上能够获取的信息犹如“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
在他看来,互联网毫无疑问带来了好处,却让我们进入了新的“无知时代”,我们急需让信息脱胎换骨,变成知识。原因在于:
互联网上的信息未经提炼和归纳,其中有着太多纷繁复杂的细节,还称不上是知识;
这个世界变得如斯碎片化,学科之间变得如斯迥异,信息变得如斯原始而未经提炼;
诸种信息需要进行综合,并将网上大量“浑浊”的现成信息整合梳理成明晰、连贯的体系。
这本书无论是叙事笔法还是视角观点都让人耳目一新,那种对历史知识、过往足迹的综合驾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大爱书中扉页里,也是送给自己的两句话:
历史让人明白,人类事务永无定论;静态的完美和终极的智慧均不可企及。
把不同的红酒混在一起也许糟糕,但新旧智慧的混合堪称绝妙。
三
人还是活的太短了,总被时代裹挟迷了双眼,也总陷入权力财富光环遮蔽的假象。
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音如同协奏曲。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每一种言论都代表了一种思潮。思潮与思潮之间相互交织博弈,各种思潮的力量随着现实环境的变迁此消彼长。共同激荡出了当下社交媒体的基本舆论场。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每一种讯息的背后,也正是一群试图推动社会变革的人群。
看到《20世纪思想史》里“达尔文的黑暗心灵”恍然大悟。历史的嘈杂只不过是在不断重演。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技术、思想以及企图利用这些技术和思想去“执行优胜劣汰”的一批人——只不过当下这种声音尤其嘈杂。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技术滋养的“新一代斯宾塞”。他不过是19、20世纪之交时英法德一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重现而已。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鼓吹“神人”——百分之一的人不受“算法“控制,相反是他们在操控着“算法”,他们不是科学家,便是政治家。
信息编织在一起怎么解读和建构都是自己的事情了,人只能做到逻辑自洽。然而也只是自己茧房内的自洽。
赫拉利信誓旦旦说,进入21世纪,曾经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你看,瘟疫真的被攻克了么?赫拉利还是太乐观了。
尼采笔下的“超人”催生了一个希特勒,也不知道不用智能手机的赫拉利这套躲在书斋里空想的东西到底会催生什么人物。
只能祈祷,不会催生出什么希特勒式的人物。然而政治极端气候之中,这种人物却极其容易振臂高呼蹦跶出来。
19、20世纪之交英法德的历史的嘈杂声音交织在一起,你总是分不清谁对谁错。大量观念塞进脑子里,以至于是如此混乱——只不过在国内当下功利至上的环境之中,赫拉利这种人,这套惊悚的理论很容易占据上风。
正如尼采、斯宾塞可以催生一个时代的疯狂。
这些历史的嘈杂并非首次。
《20世纪思想史》里记载,众多德语国家里,科学家和伪科学家、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都在争取公众关注的斗争中试图压过对方。
赫拉利无疑是今日国内互联网、创投圈最受欢迎的座上宾。他的声音显然压过了其他的声音。
CEO们在技术春药的催情下显得有些癫狂,用许知远在对话赫拉利时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对赫拉利的追捧就象是对待一个摇滚明星”。
一个宗教圣地的历史学家居然可以如此无视耶和华的愤怒,编纂出一套如此离经叛道的东西。
虽然并不敢直接否定他,但却对这种缺乏敬畏之心感到恐惧。脑海里甚至可以浮现孙悟空在如来手掌里撒尿的荒诞感。
如果把赫拉利奉为圭臬,显然是忽视了当下思潮中的其他声音,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正如历史的交响曲中,你听到了小提琴的高昂,却忽略了钢琴的柔美以及大提琴的低沉。
赫拉利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伪知识分子?他的预言到底是正确还是谬误?
历史的矛盾逆流将慢慢揭开他的面纱,交给我们答案。
四
莎士比亚深受悲剧熏陶,他强调的是“贪婪的时间”造成的毁坏。所以他在自己的十四行诗里写道:
我曾窥见时间之手的残酷,被陈腐的岁月掩埋就是辉煌的代价。
人在时间和自然的面前,还是太过渺小。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