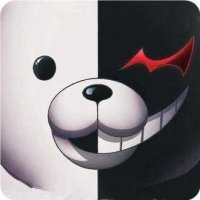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怪盗团”(ID:TMTphantom),作者:怪盗团团长裴培,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自从去年9月,波澜壮阔的大行情启动至今,中证白酒指数仅仅上涨了10%,也就是几乎没有涨;白酒指数现在的点位还不到2021年初最高点的一半。贵州茅台现在“仅仅”是沪深300指数当中市值第六大的公司,而且随时有可能掉到第八或第九大公司;五粮液的市值则仅能排到第二十七。白酒被资本市场遗忘了,就算偶尔想起来,也是当成嘲讽对象。最近一个月,我的朋友圈至少有七个人发布或转发了关于“白酒为什么过时了”的讨论。
我从来没看懂过白酒,不是因为我不爱喝酒,恰恰是因为我太爱喝酒。我在家中的工作台下方就是个酒柜,里面塞了三四十瓶各式各样的酒。厨房的橱柜里放了不止一箱红酒,冰箱里经常塞着啤酒、清酒和水果酒。冬天我爱喝黄酒,还专门搞了保温装置。工作的时候我爱喝加了咖啡的酒,咖啡世涛、咖啡朗姆酒之类的都很好,或者干脆拿咖啡液和伏特加自己调威士忌。我会万里迢迢从格鲁吉亚带回葡萄酒、从巴厘岛带回椰子蒸馏酒,哪怕为此额外付出托运费。我唯一不喜欢的主要酒类,就是白酒。
声明一下,我不是单纯觉得白酒不好喝——用“好喝”两个字点评酒,本来就是片面的。如果一定要说偏好,我比较喜欢浓香型白酒,对酱香型无感,对清香型则是敬而远之。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一个人自斟自饮,还是跟朋友聚会,我首选的都不会是白酒。因为我始终没想明白一件事情:白酒的定位。
作为一个很小就开始喝啤酒、大学期间经常泡Live House的老酒鬼,我觉得以下四件事情不应该出现在同一种酒类身上:
度数很高,超过40度(知名白酒通常为53度)。
主要饮用场景是饭桌,或者叫做“佐餐”。
一般是净饮,既不拿来调鸡尾酒,也不加冰或加水。
价格往往很高,虽然其中也有平价货,但高档货更不少。
每当有人在饭桌上招呼大家喝白酒,我都忍不住想提问:喝下几杯53度的蒸馏酒之后,舌头都麻痹了,怎么吃菜?而且中式劝酒一般在动筷子之前就开始了,我相信,经过这种劝酒,不管你吃的是山珍海味还是鞋拔子,味道都不会有太大差别。怪不得最近二十年清淡的菜系几乎被踢出中餐主流,只有麻辣、香辣、咸辣的菜系大行其道。毕竟,要让舌头在经过白酒肆虐之后还尝得出滋味,那只有借助更厉害的辣椒和花椒。
虽然也有人开发过“中式鸡尾酒”,但一般而言,白酒用于鸡尾酒的场合极少。一方面是文化因素使然,另一方面是白酒复杂的香型不太适合拿来调酒。这个世界上最流行的鸡尾酒基酒是伏特加,因为它就是纯粹的酒精溶液,没有香味。白酒的香型可能也导致了不适合加水或加冰,消费者只能拿着小杯子,硬着头皮一饮而尽——以一般人的酒量,五六个小杯子就很容易醉。
过去一年,我在北京参加过精酿啤酒节、威士忌节、龙舌兰节。精酿啤酒节很有趣,因为度数不高,坐在太阳底下的草坪上,随便一喝就是半天过去了。威士忌节要凶猛得多,因为高档威士忌的度数一般都超过40度甚至50度,我只尝试了少量净饮,就不得不改喝鸡尾酒。但最凶猛的还是龙舌兰,因为它的饮酒文化是“快饮”,把一小杯火速灌下肚然后含着柠檬片才是正道,于是我尝试了三杯就决定休战了……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威士忌几乎都从不用于佐餐。龙舌兰仅在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用于佐餐。这些国家的酒鬼听说我们整天在饭桌上喝“加浓版龙舌兰”,肯定会吓掉眼镜。记得2012年,我还在金融机构讨饭吃,某次对香港同事说:“我们这边有些人,出于工作需要,一餐要喝一斤白酒。”对方吓蒙了,反复追问:“一斤?你确认是一斤?那不会出人命吗?”我笑道:“他们为了升官发财,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喝一斤白酒算什么?”
别误会,有烈酒佐餐习惯的国家,当然不止中国一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流行在饭桌上喝高度酒,例如毛子以一边吃饭一边咕咚咕咚灌伏特加而著称。几个月前我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喝到了当地知名的“恰恰”(Cha-Cha),一种用葡萄酒渣酿造的、非常难喝的烈酒,据说斯大林喜欢拿来宴请同事。格鲁吉亚酒庄老板娘告诉我,她家有时候会自酿高达八十度的恰恰,这种东西必然不会有客人买,主要用于家庭内部聚会整蛊。
当然,无论是伏特加还是恰恰,价钱都很便宜。我以大约四十块人民币的价格从格鲁吉亚背了一瓶恰恰回来,几位朋友喝完之后毫无怨言,因为“这么便宜的酒你要啥自行车”。如果某种“高档恰恰”卖到一千多块钱一瓶……那不就是中国的茅台和五粮液吗?(我知道有人会教育我白酒的“文化属性”,但我恳请他们先研究一下恰恰,这玩意要讲故事绝不会在白酒之下。)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喝过并且买过世界上大部分已知酒类的老酒鬼,我认为任何一种主流酒精饮料,其饮用场景均可划归以下三类之一:
佐餐酒,一般是低度酒,以啤酒、葡萄酒、清酒为代表。
非佐餐社交酒,包括低度的鸡尾酒、啤酒,也包括高度的净饮烈酒。
非佐餐自饮酒,理论上可包括任何一种酒,实践中烈酒比例较高。
佐餐酒的适用范围最广,毕竟大家吃饭的时候总得喝点什么。不吃饭的时候,或者刚吃完饭的时候,大家也要社交,酒吧和夜店里卖的大部分都算社交酒。至于自饮酒则是专业酒鬼的最爱,一个人在深夜自斟自饮的时候,肯定会喝自己最爱喝、最能满足情绪价值的酒,不论是烈酒还是低度酒。
白酒这玩意显然极少用于“自饮”场景。为了防止抬杠,我得说明一下:确实会有人独自喝白酒浇愁,但是几乎仅限于饭桌上,甭管饭桌上放着的是正餐还是冷荤、花毛一体。脱离饭桌场景,在花前月下、游泳池边或者壁炉前独自一人拿个白酒杯子“举杯邀明月”,那会让人想起精神病发作前兆。
至于非佐餐的社交酒……有人会在酒吧、夜店或海滩俱乐部卖白酒吗(不管是净饮还是调鸡尾酒)?就算他敢卖,你会买吗?在正经酒吧,白酒调的鸡尾酒一般属于猎奇性质,喝个一次就算了。全世界最流行的100款鸡尾酒没有一款使用白酒为基酒。
剩下的就只有佐餐了。佐餐可能是白酒唯一重要的饮用场景,其集中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最常见的佐餐酒——葡萄酒。在全球各国,你都能找到专业的“葡萄酒吧”,提供葡萄酒净饮,最多配个奶酪或坚果盘子。我很期待有人开设类似的“白酒吧”,相信那会创下一种商业模式最快被证伪的记录。
几乎以佐餐为唯一饮用场景的白酒,恰恰是一种在本质上不适合拿来佐餐的酒,这就有点……要知道,就连发明了烈酒佐餐习惯的俄罗斯,现在都越来越不流行拿伏特加佐餐了。我有个朋友经常去俄罗斯做生意,至少在他目睹的范围内,俄罗斯人餐桌上的葡萄酒远远多于伏特加。
关于白酒佐餐这个奇怪习惯的起源,我跟朋友做过很多次探讨。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服从性测试”,其目的第一是让你痛苦,第二是让你晕乎。为什么选择餐桌作为场景,因为餐桌最适合开展此类“服从性测试”。所谓白酒文化,骨子里就是敬酒文化和罚酒文化。在这两种强大的负面文化的淫威之下,白酒丧失了年轻人的喜爱,自然退出了酒吧、泳池、起居室之类的场景。当它在自己的大本营——餐桌上,也受到各种显性和隐性限制时,它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公允地说,哪怕没有“服从性测试”这个重大的文化Debuff, 白酒曾经的流行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烈酒的消费范围都远远小于低度酒。啤酒在中国如此流行,不是因为它是舶来品,而是因为它占领了佐餐、社交两用低度酒的生态位。这个生态位以前属于黄酒,后来黄酒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衰落了。白酒在中国消费行业和资本市场风光无限是一个异常现象,现在恐怕只是均值回归。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强调几个点:
酒精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确定会增加包括癌症风险在内的多种健康风险。
酒精没有安全摄入剂量,任何酒类对健康的坏处均高于其好处。“喝酒强身”是一种文化迷思,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我喜欢喝酒的唯一原因是我管不住自己。但我努力把饮酒时间控制在四分之一以内,即:任何一天只要喝酒了,接下来至少三天不喝酒。
附带说一句:当年我在券商混饭吃时,经常遇到痛心疾首地宣称“游戏坑害小孩,所以不应该投资于游戏公司”的老基金经理。这些人一般都很爱喝酒,而且是茅台、五粮液的死忠粉丝。有时候我会问他们,游戏“害人”,白酒就不害人吗?为何不一视同仁,连白酒公司也别投资了?他们的反应大致分为两种:
坚持宣称“白酒不害人”,甚至搬出那篇著名的“茅台酒保肝护肝”的神经病论文,充分说明了他们当年没有接受过良好的九年义务教育。
坚持宣称“白酒跟游戏不是一回事”,因为“游戏害小孩,白酒害大人”,大人反正活该被害,喝死算逑。这倒是有点真性情,表里如一,我很喜欢。
总而言之,愿大家少喝酒,多享受幸福美好人生。我希望白酒行业再也别回到几年前的高度了,因为一个资本市场上最值钱的公司是出售浓度高达53%的一级致癌物的公司,怎么想怎么让人觉得不对劲。
本文为专栏作者授权创业邦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